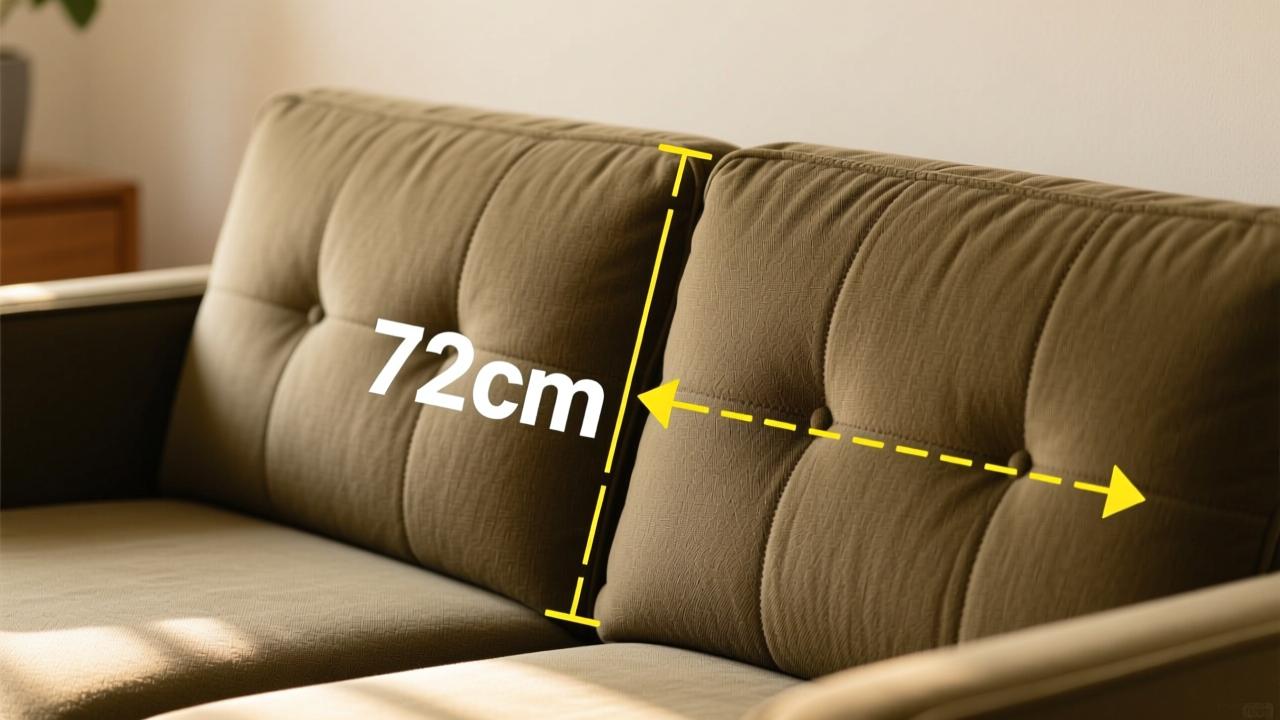马桶为什么叫马桶?揭秘宋朝避讳文化与市井语言智慧的千年演变
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老人说“马桶”,还以为真跟马有关,是不是以前骑马时用的?后来翻书才发现,这名字背后藏着宋朝人的小心思和语言智慧。

“马桶”这个词,最早不是叫“马桶”,而是叫“马子”。《东京梦华录》里写汴京夜市,提到“马子”摆在铺子里卖;南宋《梦粱录》也记临安城“诸色杂货”中有“马子、脚炉、火盆”并列。注意,这里没写“马桶”,只写“马子”,而且是和日用器物一起出现的。再往前推,唐代有“虎子”,汉代也有,但宋代人开始不用“虎子”了——避讳李虎(唐高祖祖父名),也嫌“虎”字太凶,便换了个更日常、更中性的词。“马子”就这样悄悄上位,成了主流称呼。
我查过几本宋代器物图谱,发现早期“马子”其实是带盖的长方木匣,两端略翘,像个小马鞍,悬在床边或马鞍后——没错,它真跟马有关,但不是给马用的。古人骑远路,随身挂个便器,形似马鞍,就叫“马子”。后来搬进城里住,不骑马了,可名字留下来,器物却慢慢变样:木匣加高、加圆、加桶状围壁,坐起来更稳,盛得更多。人们顺口把“马子”叫成“马桶”,不是因为里面养马,而是“桶”字把它的容器本质点破了。一个“桶”字,让名字从隐喻落地为实感。
再说那个“马”字,它根本不是动物。就像“虎子”不真画老虎,“马子”也不真画马。这是古人的语言策略:不说“尿壶”,不说“便器”,偏挑个不相干的动物字来打掩护。语言学上管这叫“秽器避讳代称”,类似今天说“上厕所”不说“拉屎”,说“方便”不说“撒尿”。宋人觉得“溲器”太直白,“便器”又太公文,不如“马子”听着轻巧、带点俏皮,还留有余地。我抄过一段明代笑话集里的对话:“客问:何为马子?主曰:马者,驾也;子者,小也。驾小车以载秽,故名。”——明明是胡诌,大家还跟着笑。可见“马”字早就不讲本义,成了一个安全又好用的语言壳子。
“马桶”这两个字,我越琢磨越觉得它像一面老镜子,照见的不只是一个便器,而是唐宋以来老百姓怎么过日子、怎么管粪便、怎么在胡同里喊一声“倒马桶啦——”,然后整条街都跟着动起来。
唐宋那会儿,汴京和临安都是百万人的大城。人一多,夜里起夜怎么办?以前用夜壶,小、浅、易洒,倒一次还得跑两趟;虎子呢,铜铸的,贵、沉、难清洗,还容易结垢。城市越长越大,巷子越来越深,光靠夜壶撑不住了。于是“马子”慢慢从床边挪到屋角,从悬着变成稳稳坐着,盖子加厚,桶身加高,底下还垫块桐油灰封的木托盘——防漏、防滑、防味。这不是换个名字的事,是整套居家卫生逻辑在升级:它不再只是应急工具,而成了家庭固定配置,像灶台、水缸一样,有位置、有规矩、有专人对接。我翻过几份南宋临安府的《厢界图》,发现有些坊巷旁特意标了“粪船泊口”,说明那时已经有人把排泄物当资源管,运去近郊种菜。马桶,就是这套城市代谢系统的第一道入口。
到了明清,马桶真真正正扎进市井骨头里。北京胡同里有“倒马桶”的营生,天不亮就推着粪车串巷,摇个铃铛,主家听见就把马桶搁门口;江南更细,苏州有“马桶巷”,杭州有“粪码头”,绍兴人甚至把马桶当嫁妆——红漆描金,内壁上釉,出阁那天抬着走半条街。我见过一份光绪年间的《嘉兴府志》补遗,写当地“晨钟未响,担粪者已络绎于途,桶声橐橐,与鸡鸣相和”。这声音不是脏乱差,是生活节奏。马桶在这里,早不是羞于启齿的秽器,而是一种被日常驯服的物件:它有编号、有归属、有清洁周期,连倒粪人都分片区、领腰牌、按月交税。它不光盛屎尿,还盛着秩序、分工和烟火气。
后来抽水马桶来了,哗啦一冲,干净利落。可大家还是管它叫“马桶”。厕所里装的是陶瓷虹吸式坐便器,广告上写“智能恒温座圈”,邻居来串门却说:“你家马桶堵了没?”没人说“坐便器堵了”。这个词没被淘汰,反而更宽泛了——小孩拉肚子,奶奶端来搪瓷盆:“快,用马桶!”工地临时厕所,工人指着铁皮桶:“喏,那不就是马桶嘛。”我问过一位八十多岁的上海阿婆,她说:“洋货再好,叫不出口。马桶两个字,从小喊到老,喊顺了嘴,也喊暖了心。”语言没跟着技术立刻转身,它拖着一点旧影子,继续往前走。那影子不是落后,是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