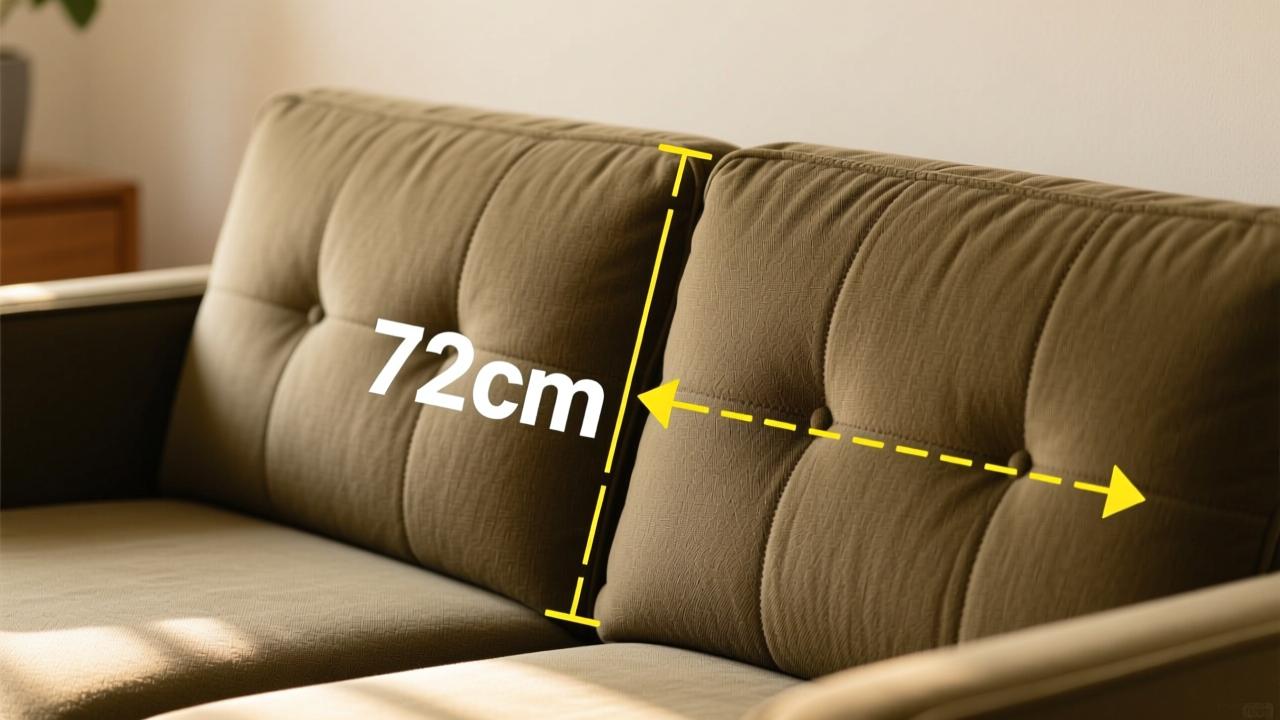白壁艺术小镇:一个被艺术唤醒的村庄,如何让平凡之地变得有灵魂
说到白壁艺术小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地方是不是墙特别白?其实不然。我第一次听说“白壁”时也这么以为,直到亲自走了一趟,才明白这个名字背后藏着一段安静却动人的故事。它不是一个被商业包装出来的网红打卡地,而是一个在时光里慢慢苏醒的村庄。这里没有喧嚣的广告牌,也没有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有的是一面面墙上的画作、一间间藏在巷子里的工作室,还有村民们脸上那种不紧不慢的笑容。

白壁艺术小镇位于中国南方的一个偏远山区,原本只是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村落。几十年前,这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房子一栋接一栋地空了下来。但正是这样的沉寂,给了艺术生长的空间。几年前,一群艺术家偶然来到这里,被这片静谧的土地打动,决定留下来做点不一样的事。他们没拆老屋,也没大兴土木,而是用画笔一点点唤醒了这个沉睡的村庄。如今的白壁,既是故乡,也是灵感的土壤。
我第一次走进白壁的时候,正逢雨后。石板路还泛着水光,巷子两边的墙上却已经热闹起来——一幅接一幅的壁画像是从砖缝里长出来的,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有孩子追着鸡跑的画面,还有谁家院墙上画着一只猫趴在月亮上打盹。那一刻我觉得,这地方不叫“艺术村”都对不起它身上的每一寸墙皮。
但你要是以为白壁只是个“墙上画画”的旅游景点,那就错了。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艺术不是被贴上去的装饰,而是像树根一样扎进了村子的生活里。几年前,几个外地来的画家开始租下空置的老屋,把它们改造成工作室。他们没打算做短暂的采风者,而是真想在这儿住下来。慢慢地,更多人来了,有做陶艺的、搞装置的、拍纪录片的,甚至还有写诗的人。这些人不争不抢,白天创作,晚上和村民一起吃饭聊天。村里原本冷清的祠堂变成了展览空间,废弃的粮仓成了小型剧场。没有人发号施令,一切变化都是自然发生的。
后来大家开始用“白壁聚落”这个词来形容这里。它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状态——一种艺术与生活不分彼此的状态。“白壁”两个字也悄悄变了味:从最初形容那些刷得雪白的山墙,到现在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有人开玩笑说,“白壁”现在是个动词了,意思是“让平凡的地方变得有灵魂”。这话听着玄乎,可当你看到一个七旬老奶奶跟着驻地艺术家学用丙烯颜料画自己年轻时的模样,你就懂了什么叫“被点亮”。
我对白壁最深的印象,是它没有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文艺样板间”。这里看不到那种刻意营造的小资情调,也没有为了拍照好看而存在的装置。相反,很多作品甚至带点粗粝感:墙皮剥落的地方照画不误,雨水顺着画角流下的痕迹也被保留下来。这种真实感恰恰成了它的品牌内核——不是展示完美,而是呈现生长的过程。它吸引来的不是流量网红,而是一群愿意慢下来的创作者和访客。
有一次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水,老板娘顺手递给我一张手写卡片,上面印着当月的艺术活动排期:周二晚上在晒谷场放实验影像,周四有村民和艺术家合办的即兴音乐会。她说:“这些事现在都算咱们村的日常了。”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要收衣服一样。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真正的融合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当艺术成了柴米油盐的一部分,没人再觉得它“特别”了。
我第二次去白壁,是冲着春天去的。三月底,山里的雾还没散尽,村子像是泡在一层薄茶里。墙上的画颜色更鲜亮了,尤其是那条主巷,阳光斜照时,整面墙像被点燃了一样。后来我才听说,这里的壁画每年都会更新一部分,有些是艺术家留下的痕迹,有些是村民自己动手添的笔。季节真的很重要——春天有新绿衬着彩墙,秋天稻田金黄,连风都带着暖色调;夏天太晒,冬天又冷清了些,所以春秋两季最值得来。
交通其实比想象中方便。我从市区坐大巴到镇上,再换乘村里定时接驳的小电瓶车,二十分钟就到了村口。也有自驾的朋友,沿着省道开进来,路上风景不错,山路弯但不难走。村里不允许外来车辆随意进入,得把车停在指定区域,这点我很喜欢——没有喇叭声和尾气,整个村子始终保持着一种缓慢的呼吸节奏。如果你打算待两天以上,建议提前联系民宿主人,他们会告诉你最近的班车时间,甚至有人会骑着摩托到路口接你。
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那条“壁画巷”。它不是一条规整的路,而是顺着地势歪歪扭扭穿进村子深处的一条老巷子,两边墙面全被画满了。有意思的是,这些画不按风格分界,前一步可能是水墨味的山水,下一步就跳成了涂鸦式的机器人摘月亮。最打动我的是一幅藏在转角处的作品:一位老人坐在竹椅上打盹,旁边写着一行小字,“他去年走了,但这儿还留着他的影子。”后来才知道,画里的人真是村里的长辈,去世前常在这儿晒太阳。艺术在这里不只是观看的对象,它成了记忆的容器。
往山上走一点,藏着几个艺术家工作室。我不敢贸然敲门,但多数人很乐意有人来访。有个做木雕的姑娘让我试了刻刀,她说工具不用多精致,关键是手要跟木头对话。她的屋子原本是间猪圈,现在屋顶还留着旧瓦,墙上挂满木屑拼成的抽象画。另一位驻留的摄影师干脆把自己的展览办在自家厨房,照片贴满橱柜和灶台,主题是“食物与离别”。这些空间没有门票,也不卖周边,你想待多久都可以。有时候你坐下喝杯茶,聊着聊着,反而比看展收获更多。

村中心的老礼堂改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陈列的东西一点都不“博物馆”——褪色的婚服挂在竹竿上,农具摆在地上,角落里一台老收音机还在播着八十年代的戏曲。讲解员是个六十多岁的阿伯,他会指着某张照片说:“这是我妈,她当年跳秧歌第一名。”语气里全是骄傲。这里没有玻璃柜隔开观众,你可以伸手摸一摸那些粗布鞋底,闻一闻旧衣柜里的樟脑味。这种近身感,是城市展馆永远给不了的。
说到吃,白壁的饭菜一点都不花哨,但特别踏实。我在一家叫“檐下”的小食堂吃过一顿饭:一碗炖土鸡、一盘野蒜炒蛋、还有一勺自家酿的米酒。老板说菜都是当天采的,鸡是邻居送的,酒是他爸存了八年的老方子。最绝的是他们家的锅巴,焦香酥脆,据说用的是祖传铁锅,烧柴火慢慢焙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村里好几家餐厅都在推“画家套餐”,十块钱管饱,米饭随便添,为的就是让创作的人能安心吃饭。
住的地方也各有性格。我选了一间由谷仓改造的民宿,屋顶挑高,睡在床上能看到星空。床单是蓝染的,图案是某个艺术家设计的,每间房都不一样。老板娘每天早上熬粥,配自家腌的萝卜干和酱豆。她说很多客人来了就不想走,有人住了半个月,白天画画,晚上在院子里弹吉他。我也理解那种感觉——在这里,时间不是用来赶的,是用来泡的。
你在白壁很难觉得饿,不仅因为吃的实在,更因为处处都有惊喜。转个弯可能撞见一个小摊,卖手工捏的陶哨子,五块钱一个;或者路过一间敞开门的老屋,里面一群孩子正趴在地上画粉笔画。没有人组织,也没有标价牌,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这种松弛感,才是它最珍贵的部分。
我第三次去白壁,是冲着“人”去的。
前两次我把眼睛留给了墙、把胃留给了饭,这次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曾经快要空心的村子,重新长出心跳?答案藏在那些不显眼的日程表里,在村民老张每天清晨扫过壁画巷的动作里,在新搬来的陶艺师小林和隔壁阿婆学腌菜的对话里。艺术在这里不是挂在高台上的展品,它成了撬动生活本身的杠杆。
4.1 驻村艺术家计划与公共艺术项目
白壁的转变,是从一封公开信开始的。三年前,当地政府联合几位返乡的文化人发起“驻村艺术家计划”,向全国招募愿意住下来创作的人。条件很朴素:每月至少完成一件公共作品,每周为村民上一堂免费课,剩下的时间自由创作。没想到响应的人越来越多,有刚毕业的艺术生,也有厌倦了画廊系统的成熟创作者。他们不要高薪,图的是安静的空间和真实的土地连接。
这些人来了之后,并没有急着刷墙画画。他们先花一个月走村串户,听老人讲过去的事,记录下每条小路的名字来历。后来出现在墙上的那些画面,很多都来自这些聊天的碎片——谁家姑娘当年逃婚跑到城里,哪棵老槐树下埋过抗战时的电台。有一面原本打算涂成抽象色块的外墙,最后变成了一幅“百家宴长卷”,画中三十多个人物,全是本村村民的真实肖像。
公共艺术也不只是视觉的。有个声音艺术家在废弃水井里装了感应装置,风吹过时会传出不同音高的嗡鸣,像大地在呼吸;还有人在晒谷场做了个“光影钟”,用太阳投影标记农事节气。最让我触动的是儿童活动中心外那堵“会说话的墙”——用手掌贴上去,就能听到孩子们用方言念童谣的录音。这些作品没人看管,雨淋日晒也不修,村民们自己补漆、清理杂草,已经当成自家的一部分了。

4.2 白壁模式对周边村落的辐射影响
白壁火了之后,附近几个村坐不住了。有人照搬搞壁画街,结果画完就没人来;也有人想复制艺术家驻留制度,却卡在配套跟不上。后来大家发现,真正能被复制的不是形式,而是逻辑——先让人回来,再让事发生。
离白壁八公里远的青石村,原本只剩二十多个老人留守。去年他们请来两位参与过白壁项目的策展人,没急着动工,而是组织了一场“记忆征集”:收旧衣服、老照片、祖传工具,然后办了个临时展览叫《我们还没走》。展览火了,年轻人陆续回来看看,顺手把自家荒院收拾出来改成茶室或书屋。现在村里有了“慢工坊联盟”,五个村子轮流办市集,卖的都是本地手艺:竹编灯罩、土布围裙、柿子醋。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影响正在反向流动。城里美术馆开始主动联系白壁的村民艺术家,请他们去办个展;一些高校把这里设为社会实践基地,学生来了要先跟着农户干三天农活。有个研究生写论文时说:“这不是文化扶贫,是文化再生。”的确,白壁的意义不在它出了多少网红墙,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个事实:当艺术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沉进泥土里,它反而能长出更大的力量。
我走那天,碰见一个背着画板的小女孩蹲在巷口写生。她画得不算好,线条歪歪扭扭,但神情特别认真。我问她画什么,她说:“我在画昨天那朵云,它飘过红房子的时候,颜色特别像妈妈煮的红薯糖水。”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在生长了。
我第四次去白壁,不再只是看,而是开始“做”了。
前几次我把相机举得高高的,生怕漏掉一面墙、一扇窗的细节。这次我放下了镜头,换上围裙,蹲在巷子尽头的工作台前,跟着一位剪纸阿婆学叠“五瓣花”。手指笨拙地翻折红纸时,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有些故事,眼睛看不见,只有手能记住。白壁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已经完成的艺术,而是它愿意把笔递给你,让你也成为创作的一部分。
5.1 参与壁画创作工坊与手工艺课程
在白壁,游客不是旁观者。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走进“共创工坊”,领一块墙面区域,在艺术家指导下参与壁画绘制。别担心不会画——这里的规则是“不追求完美,只表达真实”。有人画自己童年记忆里的灶台,有人描旅途途中遇见的一只猫,还有孩子用歪歪扭扭的线条写下“我想住在有彩虹的村子里”。这些画面或许不够专业,但正是这种“未完成感”,让整条壁画巷像一本持续更新的日记。
除了涂墙,村里还开了十几种手工艺课:陶艺拉坯、蓝染布艺、竹编小筐、土法造纸……每节课都由本地匠人或驻留艺术家亲自带。我试过一次陶轮体验,老师傅不说技巧,先让我闭眼摸泥,“听它的脾气”。泥巴转起来的时候总歪,急得我满头汗,他却笑着说:“慢一点没关系,它也在适应你。”最后那个歪脖子小罐我没带走,就留在工坊架子上,标签写着“某年某月某人第一次捏的梦”。后来听说,有游客专程回来找自己的作品拍照。

这些课程不贵,三十到八十元之间,包含材料和指导时间。更重要的是,它们不是流水线式的打卡项目,而是鼓励你留下痕迹。有个上海来的女生连着三年暑假都来,从零基础到现在能独立完成一幅墙绘,去年她带妈妈一起来,母女俩合作画了一面“厨房回忆录”——锅铲、辣椒串、老式煤炉,全是她们家的老物件。她说:“在这里,我不是游客,我是这个村子一点点变好看的过程里的一粒沙。”
5.2 白壁艺术节与年度文化活动日程
如果你想知道白壁什么时候最鲜活,那就盯紧每年四月的第一个周末——那是“白壁春醒艺术节”的开幕日。全村变成一个开放式舞台:清晨六点有“大地声音计划”,艺术家带着大家用锄头、水桶、风铃即兴演奏;中午在晒谷场摆百米长桌宴,菜是村民做的,餐具是游客自己画的陶碗;下午孩子们拎着颜料桶冲向指定墙面,开启“童画风暴”;晚上整个村子熄灯,只剩墙上荧光涂料闪着微光,像星河流进了巷子。
除了春季大节,全年还有不少值得专程赴约的活动。六月“夏夜民谣夜”,本地乐队和路过歌手在老祠堂前弹唱,观众席地而坐,啤酒杯里浮着冰镇杨梅;九月“丰收剧场”,村民自编自演的短剧在田埂上演,讲的是几十年前如何抗旱抢收,台下坐着的年轻人边笑边抹眼泪;十一月的“交换节”最有意思——你可以拿一本书、一件旧衣、一首诗,去换别人的手作礼物,不许交易,只许“心动匹配”。
这些活动从不靠强推宣传,全靠口耳相传。我在民宿墙上见过一张手绘年历,上面密密麻麻标着各种日程,旁边贴着便签:“今年我要学会扎灯笼”“等女儿放暑假再来参加绘画马拉松”。就连村口卖冰棍的大爷都能随口报出下个月的日程:“23号有陶艺快闪,26号要修东头那堵墙,志愿者报名找穿蓝布衫的小林。”
我最后一次离开白壁时,背包里多了个沉甸甸的东西——是我自己画的那块小瓷砖,上面是一只飞向太阳的笨鸟。民宿主人说,他们会把所有游客做的作品编号存档,将来建一个“人人美术馆”。我不知道那一天会不会到来,但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匆匆按快门的外人了。
在这个墙会说话、泥有温度的地方,每个人都能找到一支笔,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句。